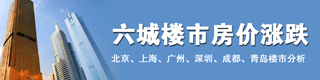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当我还是纽约的一名建筑学生的时候,我和同伴们所敬仰的建筑师大多属于在竞标中落败而出名的一类,对于我们来说,落败只不过表明他们的设计对文化机构来说太过激进、太大胆了。

这并不仅仅是年轻的理想主义。如果能从世俗的诸如预算、客户和规划法案等职业考虑超脱出来,这些建筑师创造出的作品定能具备审美意义上的创造价值和犀利的社会评论价值。并且他们的设计具备广泛的影响力,被寻求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理想的年轻建筑师所仔细效仿。

已年满68岁的伍兹先生正是当年建筑潮流的标准固定成员。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他出版了已系列震撼的设计图稿,尝试探索建筑与暴力之间的交叉点。首当其冲的便是柏林自由区项目(BerlinFree-Zoneproject),设计紧接着柏林墙的倒塌完成,其构想被作为一种社会动荡年代也为创作自由提供了机会的阐释。

进攻性的机械状结构——其钢铁外表类似战争残骸——被植入被遗弃的建筑废墟,这些建筑的一侧就是柏林墙曾经的死亡地带。建筑的外观被故意设计成难以分辨的怪异形状,根本就不适合居住————这是将典型的中产阶级(bourgeois)摒弃的一个策略。“你不能把你的旧习惯带到这儿来,如果你想入伙,必先洗心革面。”他警告说。
一些评论家对该设计的冷血景象进行了指责。但该设计其实颠覆了冷战时期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建筑师都在努力地为建造一个和平年代的天堂而对战时军备产品进行改造。其结果之一是,设计思想僵化的郊区扩建项目泛滥。而与之相反,伍兹先生从来就不是乌托邦化的人。其建筑图稿所演绎的社会似乎布满裂缝。他设计的反光的隔离舱被保护起来以对抗周围的杂乱,似乎是专为被放逐者、叛逆者、异教徒以及梦想家这样的社会弱势人群设计的庇护所。
·利布斯·伍兹:放逐的的异端建筑师 08/09/17
·观念:“我是建筑师,我不是政客” 08/09/16
·高迪的房子 08/09/15
·迪拜的未来 08/09/15
·建筑学院士与易学家之间的对话 08/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