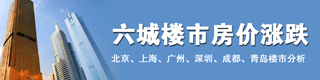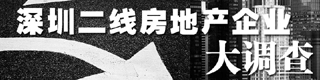这个本应逐渐趋于平庸的青色之城,似乎摆脱了其一直以来的模糊面目,开始清晰于世人眼前。

青色
“青色之城”呼和浩特,作为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在汉唐时期,这里就是中原地区开展对外交往的重镇。
无论是远古时期的“大窑文化”遗址,还是战国时期的云中古城遗址,或是明清时期的召庙艺术,都忠实地记录着呼和浩特的悠久历史以及塞外名城的古老神韵,这一切伴随着古曲“敕勒川”跨越千年的时光,让人沉迷至今。
不经意间,今日呼和浩特的春天会突然从北方吹来一阵沙尘暴,随后的天空就像撒哈拉沙漠的上空一样,弥漫着尘土。但是没有沙尘暴的呼和浩特的春天,云淡风轻,纯洁无暇。
到了夏天的呼和浩特显得异常繁忙,白天,大伞小伞穿梭在大街小巷;晚上,地摊琳琅满目,有啤酒,有烤羊肉,有牛板筋……
而秋天的呼和浩特很凉爽,翻过大青山就是一片干秃的土地,但并没有草原,没有羊群,没有雄鹰翱翔在天空,只有蓝天白云。
冬天,凛冽北风呼啸而过,吹裂鼻孔、脸孔,人们都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穿着厚高的皮靴,在雪地里留下大大小小的脚印。
翻寻史书,呼和浩特得名与1581年阿勒坦汗(俺答汗)在云中旧地筑城有关——用无数青砖筑就的城墙远望一片青色(蒙语“呼和浩特”),所以人们称之为“青色之城”,明王朝赐城名“归化”,清康熙年间被更名绥远。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作为绥远省城的归绥城(归化与绥远合称而成),与绥远一道并入内蒙并被更名为呼和浩特。
虽然“青色倾城”,但是呼和浩特一直以来似乎只是一个带有蒙古草原印象的北方普通城市。
过去,呼和浩特可以被概括为一个以毛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城市,但今日的呼和浩特在商业文化冲击下,却连这个特色也难以保持。最后虽然保存了一个“乳都”的称谓,面貌却与其他的北方城市似乎没有任何区别——在尘土飞扬、拥挤与嘈杂中不断发展着,并日益繁荣。
步入城市,首先迎接而来的是破旧低矮的80年代前留下来的前苏联风格的“火柴盒”,这些与其他城市并无二致的红砖民居,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建筑风格。但举目远望,却也矗立着不少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多少年来,也许这个城市留下的惟一标注本地与北方其他城市有不同文化历史背景的建筑,只剩下内蒙古博物馆了。
这是一座由西南方向东北方生长拓展的城市,现在则是东西走向,如果说西南是它的过去,那么东面则是它的将来。一系列大手笔的城市规划使这座城市的面貌终于有了与塞外第一大城匹配的气度与格局。
作为草原文化的中心城市,呼和浩特一直面临着发展经济而失去文化,还是保存文化牺牲经济速度的两难境地。或许,文化一旦与商业扯上关系,最终只会带来草原文化被更快地吞噬的恐惧。
从80年代之前全国一致的红砖民居、80年代全国流行马赛克、90年代瓷砖贴面铝合金门窗楼,到2000年后的玻璃幕墙塑钢门窗楼,再到近两年突然兴起仿西洋古建筑风格。整体文化品味的缺乏和商业审美的急功近利,总是使得中国各个城市在风格上显得如此的雷同,如白开水般索然无味。
曾经的呼和浩特也没有逃脱“恶俗”,也不可能逃脱。但今天回首处,仅仅才建设钢梁的呼和浩特东站,却有着一个典型的成吉思汗金顶大帐的轮廓,与中国各地新建的当代风格车站差异之大,以至于让人不禁眼前一亮。而今天呼市正在使用的火车站,则与中国任何一个老式车站没有任何不同。
这个本应逐渐趋于平庸的青色之城,似乎摆脱了其一直以来的模糊面目,开始清晰于世人眼前。
大召寺:庙宇内外的世界
蒙藏文化街、伊斯兰风情街、蒙满特色街、成吉思汗大街……在这许许多多风情各异、嘈杂喧哗的地方文化特色街区拱卫中,大召寺更显其宁静与肃穆。
呼和浩特城内有大小庙宇50多座,东南部有华贵雍容的五塔寺、金碧辉煌的席力图召、气势轩昂的“银佛寺”大召、规模宏伟的北门外清真大寺、珍品云集的新华街东口博物馆、博大精深的“广化寺”喇嘛洞召、昭君墓、乌素图召、万部华严经塔(白塔)等大大小小的佛寺庙宇。
其中最著名的即是“召庙文化”,事实上,早在明清时期,呼和浩特地区就寺庙众多,被称为“召城”,在民间素有“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绵绵召”的说法,诸多召庙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召寺。
有着四百余年历史大召寺无疑是其中最灿烂的佛门奇葩。从明朝至今,它一直是内蒙古佛教活动的中心。
一般意义上,佛门是神圣的所在,无论在信徒还是在一般人眼里,似乎都意味着纯洁、雅静、庄严,与虚假、浮躁、杂乱格格不入。而在苦寒塞外能有这样气势宏伟而又庄严肃穆的佛门圣地,无疑足以令人感到惊讶。
大召是蒙汉“合壁”的一种称谓,它的蒙古语称谓是“伊克召”,“伊克”译成汉语是大的意思,“召”则通常译成“寺庙”,所以后人采用蒙汉合壁的称谓,把这座寺庙称之为“大召”,译成汉语就是“大庙”。大召寺是由明代蒙古土默特部落的首领阿拉坦汗于明万历七年(1579年)主持创建的。明廷赐名“弘慈寺”,清代后改称“无量寺”。
大召寺的建筑风格是藏汉结合,寺院面积约三万平方米。分东、中、西三路,中间一路为主体建筑,山门位于南边,上悬“九边第一泉”匾额。相传康熙皇帝路经此地,人马皆渴,他的马能识别地下水源,由马引路,找到了八眼泉井,水质清甜。万历十四年(1586年),达赖三世索南嘉措来到呼和浩特,亲临大召,主持了银佛“开光法会”,从此大召成为蒙古地区有名的寺院。
这里属于藏传佛教中的黄教格鲁派,这是一个陌生而又让人敬畏的宗教教派。
呼和浩特不时刮起的阵风,让大召寺悬挂的旗帜上的铃铛幽幽响起,从前院和树间到人耳,像是从远处飘来有人低声呢喃的声音,交杂着风沙绕着炉火转,不信鬼神的人在这里也不能不收起对宗教的无知及狂妄,谦卑的在四大天王眼下低头弯腰安分经过。
寺里永远都不缺少游人与信徒,游人中有的虔诚、有的逢场作戏,但信徒们却始终如一,虔诚地绕着每个喇嘛磕头,而喇嘛会拿起手里的经书轻轻的触碰他们的头上,犹如洗礼,更如点化。有母亲流泪,有人始终弯腰低头谦卑至极。这样的祈求、宽容和祝福,或许真能为受苦的民众换得一些人世的安慰和希望。祈祷,是他们眼中和希望最贴近的姿势。
那种浑厚低沉的诵经声和法器钟声,似乎可以让从没耐心摒除杂念打坐的人,也会在这里意外沉迷,接受智慧和平静无微不至的洗礼。
如果说宗教能够带给人心灵的宁静,那么在宁静之下承载的却是不变的麻木与淡漠。或许麻木能够抚平伤痛,淡漠能让人远离苦难,但是那些虔诚的喇嘛与信徒的生活,似乎不是整天以奔波为乐的人所能理解的。在普通人眼中,这个寺院也许就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另类世界。
在围墙里面是一个世界,围墙外面又是一个世界,大雄宝殿外的天井干净温暖,抬头便可见朗朗的蓝天白云和暖暖的太阳,让人恨不能把一切伤心、苦闷、得失都翻出来晒晒。
佛是千年不变的慈祥,来往朝拜者却是日新月异的面孔和千奇百变的愿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仿佛一直以来只存在于信徒们的梦想之中。他们所有的愿望都是最本原、最生动、最感人的东西,都没有理由,一如佛对世人的爱。
“青冢”昭君古墓
昭君墓始建于西汉时期,距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现在的昭君墓是20世纪70年代重修的。墓占地3.3公顷,墓高33米,是用人工将土堆积起来夯筑而成。当然,这只是王昭君的一处“衣冠冢”,也是官方指定的昭君墓。
如今的昭君墓,已扩建为昭君博物院。陵园内除昭君墓外,还有匈奴文化博物馆,昭君故乡建筑等。昭君博物馆里有董必武六十年代《谒昭君墓》诗碑,诗曰: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传说每年九月秋凉、塞外草衰时,唯独昭君墓上依然芳草青青,故后人称之为“青冢”。
关于“青冢”也另有解释。《筠廓偶笔》:“王昭君墓无草木,远而望之,冥蒙作青色,故云青冢。”《塞北纪游》上也写道:“塞外多白沙,空气映之,凡山林村阜,无不黛色横空,若泼浓墨,昭君墓烟垓朦胧,远见数十里外,故曰青冢。”昭君名嫱,西汉南郡秭归宝坪(今属湖北省兴山县)人。汉元帝时被选入宫,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和亲,致昭君远嫁匈奴,后立为宁胡阏氏,仅仅两年后,年迈的呼韩邪单于身死,王昭君忍受屈辱成为了新单于(有说是呼韩邪单于之弟,有说是呼韩邪单于之子)的阏氏。甚至可以说,王昭君以一己之身,换来西汉边塞的六十多年平静。
昭君出塞,史书上记载是她的大义和贡献:“边城晏闭,牛马布市,三世无犬吠之惊,黎庶无干戈之役”。但是,“红粉飘零,远适异域,历经千年,只余黄土”,百姓感念的是她为民族不惜舍身,痛惜的是她孤身远嫁匈奴。在民间,她是美的化身,数千年来,她的传说、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现代史学家翦伯赞说:“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虽然那种友好,只是暂时的。
古往今来,有关王昭君的诗词不完全统计有700余首,其中杜工部《咏怀古迹》更是入骨三分:“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两千年的历史长河淹没了太多的事实,让真相与传说一起流传,最终难辩真伪。后人不仅对青冢有所争议,就连对王昭君和亲事迹的叙述是否属实,对王昭君出塞的原因,王昭君名字的由来是否如述都有推敲。
无论推敲与否,不能否认的是,正如翦伯赞所言,王昭君已经变成一种象征,文人寄托幽怨与哀乐,国家寄托安宁与兴亡。
昭君不是出塞的第一人,汉族被迫和亲也不只汉代一朝。无论如何,王昭君以民女身份和亲匈奴,远比汉室公主的出塞更为深入民心,又或许,其下嫁呼韩邪单于,多多少少都带有汉帝国对暂时臣服的匈奴的一种恩赐的意思,所以,双方的和平来得更加容易。而民众的同情与关切,民间的演义与传奇、野史的记载与评述、文人的吟咏与赞叹,均使这样一个绝色的女子,留在天空上,朔漠旁。
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自有华夏一族,中原大地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被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侵袭的命。即使长城万里,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坚固壁垒;或许,汉家史上,惟有西汉武帝时期,是真正强大而不惧外患,但也曾有计拙而和亲之痛。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种无奈与悲哀,延续数千年之久。即使是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豪言壮语的西汉元帝一朝,也有王昭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