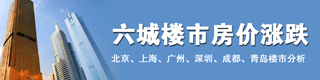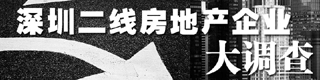相信很多读者对隈研吾的了解都是从长城下的竹屋开始的,他用竹质材料建构了一个与长城两两相望的独特空间,几乎是不可思议地实现了“结庐在人间”。好奇也罢,赞叹也罢,当你平心静气地读完这本《负建筑》,也许能更深刻地领会他为什么会做此种选择。
“有没有可能建造一种既不刻意追求象征意义又不刻意追求视觉需求的建筑呢?正是在这样的悲观氛围中,我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也由此诞生了这本书,并取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书名——《负建筑》。”环顾我们的四周,“象征意义”和“视觉需要”似乎已成为建筑的使命,而他为什么对此感到悲观呢?“所谓‘负建筑’并非是输的建筑,而是指最适宜的建筑。”隈研吾曾经这样向我解释他为什么以此来命名他理想的建筑。这其中虽然存在日文与中文语义的细微差别,但我想还是可以看出他对建筑因为被赋予过多的寄托而偏离其本初面目的一种澄清。
在这本书中,隈研吾并没有一一列举他自己的建筑案例,而是把目光投向更广袤的世界。叙说的起始——1995年,在他看来是一个危机之年。阪神淡路大地震、奥姆教毒气事件……一直到6年后的“9·11”事件。建筑物作为人类的庇护所竟是如此脆弱。但他对“脆弱”的指认并非局限于其物理属性,而是从建筑的建设者、拥有者和使用者的立场出发,指出是其私有属性决定了它的脆弱。这种认识使他的关注对象不再只是建筑本身,他的言说也由此不再只是一个建筑师在专业领域内的喃喃自语。
但他的质问和追索并未因此失于空泛。在我看来,这本《负建筑》对于了解现代建筑的种种症状也是很有裨益的。密斯、柯布西耶这两位现代建筑大师在隈研吾的笔下似乎有了更为生动的面目,他对鲁道夫·辛德勒似乎带着一丝痛惜,而他对村野藤吾的击赏更是让我们也更为深入和全面地了解了他本身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
我们的欲望让我们把建筑物从周围环境中分割出来,我们忘记了建筑的本意是让我们容身,让我们居住地更舒服,而一味地将建筑当成“物”,在其身上画满了各种符号,直至将我们自身淹没。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隈研吾最想表达的。而他自己也是由此出发,在现实中努力设计和建造“负建筑”——最适宜的建筑。
·北京城的前卫建筑 08/09/03
·合景泰富:领峰——国际级都会核心豪宅 08/09/03
·鸟巢的后半生 08/09/03
·上实控股中报:房地产业务纯利2.5亿港元 08/09/03
·上海商业银行14亿购得中航大厦 08/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