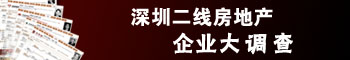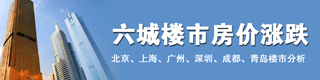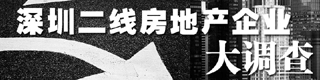这里并没有严寒的冬天,但如此盛开的花朵,依然能在这个超级大都市的环境里,代表着一种生机与希望:那种每位纽约客都深信会发生某种变化的希望。
八个月前,我搬到曼哈顿去参加库曼中心(Cullman Center)的一项奖学金计划。通过这项计划,库曼中心为15位作家与学界人士提供研究撰写下一部作品所需的办公场地和津贴。今年这项计划囊括的内容有:以上世纪80年代萨格港(Sag Harbor,注:纽约州的第一个通商口岸)为背景的一本小说、一部关于美国国会内部纷争的历史作品、来自新泽西的一位单人表演喜剧演员的传记,以及一项关于黑奴解放运动的研究等等。因此可以说,库曼中心还为我提供了一个迷人的美国历史万花筒。通过它,我可以纵观这个国家当前发生的种种事件。
我了解到,当前的美国大选并不是第一次以“改变”为主导词的总统选举。回望1864年,林肯(Lincoln)在竞选连任时就忠告美国公众:“不要在趟过溪流的中途换马”(Don‘t change horse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am.)。但这句口号却被对手麦克莱伦(McClellan)偷梁换柱。麦克莱伦对选民们说:“要么换马,要么被淹死。”(Change horses,or drown.)
再将时钟拨快150年,就可以看到,民主党(Democratic Party)内争取提名的几位候选人在代表“改变”观念的同时,也在大谈特谈所谓“改变”。不过,看上去并无改变的,是这些候选人期图能游走其间的公众话语的本质。自然,竞选口号仍会被盗用。同样存在的,还有媒体对咬文嚼字的偏执,以及对杰弗逊(Jefferson)式人民代表的需要。结果,随着竞选的持续,这场公开辩论的水平有时看上去已变得缺乏智慧,而且越来越跑题。在这条战线上,唯一让人觉得事情确实发生了改变的场合,是当有人指控奥巴马(Obama)支持发表煽动性言论的牧师耶利米?赖特(Jeremiah Wright)时,奥巴马所回应的讲话。我已经记不清,还有哪位政治人物的讲话能让我这么不想出门。不过,这正是我从广播里偶尔听到奥巴马在费城(Philadelphia)讲话时的感觉。重要的不仅是他能直接面对这个沾染恶名的原始主题,还在于他那种诚实的态度,以及他愿意去体解争辩双方的不平情绪、并试图寻找一种团结向前的方式。此时能被真正称为转变的,是一位政治人物将有关指控转化为道德的论题,而这个论题已超越了他讲话的具体场合。
曼哈顿这个岛屿的定位,来自于持续的变化,以及19世纪作家西奥多?德怀特(Theodore Dwight)所谓“忙碌者的恒久运动”(“perpetual motion of the busy”)。每年都有数量惊人的历史建筑被拆除。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建筑的旧外壳又会被重新构建。夜晚时分,曼哈顿街道的道道伤口会被揭开,城市里那些内脏一般相互缠绕的管线则任由人粗暴处置。清晨时节的曼哈顿上空,处处可闻建筑工地的声音。街面上一间曾是妓院的熟食店,相继变身为美甲店、咖啡屋,之后又变回到熟食店。一间间的店铺、公寓和宅院里,无不游荡着往事的幽灵。
这种地貌变迁的感觉,一旦联结上你与800万人跻身于同一座小岛的切实生活,你也许就并不奇怪,为何初到曼哈顿的人会很容易培养出一种特殊的地域感。他们会在熟悉的地带搜寻出熟悉的通途,就像是在城市的密集脑部里形成一条条神经传递的路径。
我的一处神经节点就是“劳伦斯家”(Chez Laurence),这是麦迪逊大道与38街之间的一家法式蛋糕和咖啡店,它正好坐落在我早晨去图书馆的路途当中。每天我都到那儿停下来喝杯咖啡,然后再开始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直到上周一这一切结束。当时,等我到了那儿,才发现咖啡店已经关门。仅仅是在上一周,店里的服务生还告诉我,“劳伦斯家”的经营历史已满45年了。透过昏暗的玻璃橱窗,我看到这个地方已被稀奇古怪地重新布置了一番。桌子被推到两边,上面堆满了厨具。柜台上放了一堆堆的银器。而每样东西上面都贴了个标签。两天前我还坐过的那把椅子,我用过的那个盐瓶,甚至是我看着点餐的那块黑板牌:所有的东西都被标价待沽。我一边走着,一边感到心头的纷扰,像是这个变幻莫定的城市,在一霎间就抽空了我脚下的依凭。我只有去另一处街角,寻另一间咖啡店,以便开始我在纽约的生活。
看来,有些东西永远都不会改变。我刚来这儿的头几个月里,不断有人告诉我:我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来,或是90年代来,或是住在布鲁克林(Brooklyn)的邻近地区,或是去年来也好。在领教了这一类怀旧情绪的滋补之后,我瞅准珍?莫里斯(Jan Morris)来访的机会问她,她在纽约看到的最显著变化是什么。珍是一位旅行作家,她在50多年里遍历全球,在写作生涯开始时用的笔名还是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orris)。我想,珍很可能知道一星半点关于变化的事情。况且,自1952年以来,她每年都要来一趟曼哈顿,所以一定知道不少关于纽约变化的事情。
她说没错,这个城市确实总在变化。“不过”,她又补充道,“曼哈顿的全部意义,而且能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城市的地方是,在内心的深处,它从不改变。”欧文用的笔名“尼克博克”,后来也就代表了纽约人的彻底本质,并同时包含了变与不变的潮流。而欧文本人也会认同这一点。对此,我表示怀疑。
对于一座如此密集的城市来说,曼哈顿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将自然的世界重叠嵌入到玻璃、混凝土和钢铁耸立的高廊之间。现在的这个时节,比一年里其他的时候更能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点。在上一个星期,曼哈顿的花草树木四处盛开。而且,常常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市中心帕克大道(Park Avenue)中段有一整排的木兰树;第三大道(Third Avenue)办公室屋顶上,一丛山茱萸正在绽放;在一间停车场的入口处,是一簇簇红色的郁金香。在这个时节,这个城市的居民同样也像花一般地绽放。你能从人们的脸庞上一次次地看到它:当人们等候在路口的樱花树下;当他们走在布赖恩公园(Bryant Park)里,并从熟悉的汽车尾气中捕捉到黄水仙和丁香的芳香时。这里并没有严寒的冬天,但如此盛开的花朵,依然能在这个超级大都市的环境里,代表着一种生机与希望:那种每位纽约客都深信会发生某种变化的希望。
作者是《抗拒》(Resistance)一书的作者(现已出平装本)、诗人和萨默赛特·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Prize)的得主。
译者/李晖
·诗人眼里的纽约 08/09/02
·德国:经济复苏的绿色印记 08/08/31
·未来20年中国将建5万座摩天大楼 08/08/29
·阿拉伯现代美术博物馆 08/08/28
·让时尚摇滚起来! 08/0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