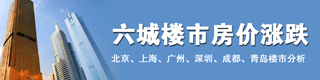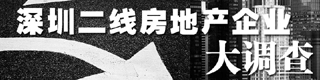诞生于疯狂年代的新兴名词——“温州炒房团”,仓促间走进历史。
“除了北京SOHO的两层办公楼,其他的房子都清空了。”8月,来自浙江瑞安的汽摩配行业老板吴先生在温州接受采访时说。
他不得不承认,属于自己作为温州炒房客的时代,那段手中拎着大袋钞票,动辄买下整层、整栋楼的豪气时代,现在已一去不返。
与早年高调进军全国不同,这次的撤离几乎悄无声息。温州某报记者发现,与鼎盛时,一两天便能组一看房团相比,“这段时间外地开发商想来温州组团的减少了很多。即使做广告,十多天都难组成一个团”。
另一标志性的特征是,被喻为“温州炒房团”重要推手的房产中介公司也渐陷惨淡。“去年7月成交量就开始下降,现在我们已经关了6家门店。”温州中介公司海螺置业的人士介绍说。
也在8月,浙江本地媒体已经正式宣告,“作为温州炒房团的最后鏖战之地,北京的寒冬标志着温州炒房团将成为历史名词。”
在宏观调控之手逐渐扼紧时,保全成了温州人当前的主题,温州热钱,正从楼市全线退缩。一个诞生于疯狂年代的新兴名词——“温州炒房团”,仓促间走进历史。
溯源龙港
出温州城往南,一路跨飞云江大桥,沿鳌江溯源而上,便是温州最早、规模最大的炒房团的发祥地——苍南县龙港镇。
这座以“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闻名的小镇,如今呈现出的是十足的繁华工业城市姿态,二十余年来,对于生存之地的惶惑,几乎吞噬了这里的每一块田地。
最初的骚动源于1984年。一直坐镇北京的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以题词方式支持深圳特区改革,也以特殊的方式支持了另一些人的大胆尝试。同年在温州,一个奇迹般的造城传奇由此而生——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镇横空出世。
龙港的建设甫一开始就带上了炒卖地产的色彩。时任龙港周边的钱库区区长的陈定模,向县委倡议由苍南每个区在龙港镇建一条街,发动先富起来的农民,到龙港投资落户。
温州基层官员的大胆和狡黠直接促成了这个奇迹。龙港的官员们在县委支持下,以收取市政设施费为名,按不同地段把土地分为不同等级,开始大规模有偿出让土地。更重要的是,陈定模从1984年的一份中央文件中,找到这样一句话:“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作为回报,县委规定,凡在龙港镇购地建房、经商办企业的农民都可自理口粮迁户口进龙港镇。
现实需求很快被证明真实存在。彼时的温州,数量庞大的农民富人群体开始形成。他们从家庭作坊式的半手工制造业起步,一双脚板走遍全国。但“商业流浪”生涯,加深了惶遽,他们急需更可依托的保障。
成为“城里人”的诱惑和对土地与生俱来的渴望,击中了农民的心脏。他们从苍南、平阳甚至文成、泰顺等地赶来,掀起了温州历史上最早的一拨炒房潮。
二十年后,有文章回忆当时的情景,“农民们争先恐后把一捆一捆的钱往柜台里塞,镇政府只得临时组织民兵到现场维持秩序!”数万名长期以来失去国家政策保护的农民,趁着制度约束稍微放松的时机,告别了乡村,迁入自己建造的城市——龙港。
“土地是财富之母。”当马克思在《资本论》引用的此语被陈定模用来印证自己的合法性,温州的农民们比他更早读到了其中的真谛。人少地多,是矛盾,更是商机。
“大家都在卖地基,转来转去。”51岁的龙港居民老杨回忆说,1984年建镇初始,一间房子的地基,费用不到千元,但经过重重倒手,到1987年,已达4000元。而一间龙港镇区相对偏僻的三层落地房,建镇时的建筑成本不过6000元,但到他1991年购买时,价格已飙升至16万元。
龙港的崛起第一次让温州人懂得了倒卖房产的巨大利差。在龙港的试验,很快被推广至整个苍南和平阳两县各镇,温州或者中国历史上第一轮的集体炒房行为由此而生。
地区性的炒楼在1996年几至顶峰。当年,已是商人身份的老杨置换一套位于龙港站前路的落地房时,单价已近万元。而同时期的杭州甚至上海,最佳地段的房产,单价才在2000元左右徘徊。
但疯狂过度必是癫狂。苍南等地的楼市在1997年前后突然陷入了冰冻期。“最高跌幅70%,个别地方回落到原来的30%甚至更低。”一位当地的中介者介绍说。而中国大地上,楼市的初春才姗姗而来。
“你能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别的地方买房了吧?”老杨解释说。
北上沪杭
游戏注定并未结束,只是转移了战场。“上海的蓝印户口是温州炒房团初期的另一个转折点。”温州的一位资深房地产人士说。1994年2月,上海对外来常住人口首次实行蓝印户口政策,规定在上海投资、购房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可登记加盖蓝色印章以示户籍关系的户口凭证。
温州人蜂拥而入。“大家都是冲着上海的蓝印户口而来。”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当年,周先知先觉,在上海火车站附近购得一套房子,成为最早在上海购房的温州人之一。
温州冰冻的楼市和上海户口的诱惑,加剧了抢滩上海的热潮。1996年入读龙港某中学高一的吴娟回忆,她的同学当年尚都居住本地,到了第二年,同学家纷纷在上海置业,1999年,高三毕业后聚会时,近半同学已迁居上海。
杭州是温州人第二个热衷的城市。1999年,杭州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原来破烂的省城,开始大兴土木,而此时,杭州最好地段的楼价不过两千元每平方米。
温州的媒体同行分析说,温州农民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对产业转移的担忧,直接促进了沪杭楼市的兴起。
温州地少位偏,“以前出门高速都没有,到杭州都要坐14个小时的卧铺。”僻处一隅的结果,是造就了王均瑶(均瑶集团创始人)“胆大包天”传奇背后的市场和企业的外移。
“我们到各地去买商铺、买房,就为外出发展打基础。”京沪两地游走的苍南印刷商张明(化名)说,无论如何,与温州相比,“上海、杭州等这些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展快,生活环境又好,当然会是我们选择的重点城市。”
与住宅相比,商铺有着更好的投资潜力:高回报,升值快,又不易贬值。人们很快发现了投资商铺的巨大利益。平阳鳌江镇的一位人士,1999年在杭州文一路花350万元,购买了7间大商铺,待到2001年转手时,价格已飙至680多万,几乎翻了一倍。
“媒体炒房团”
抱团确是温州人的传统。从早期苍南猖獗的走私,到其后游走全国的温州业务员,其庞大规模的背后,正是自南宋传承至今的浓厚宗族乡土观念和互助的经济传统。
一个温州人到某地经商,生意做大后的第一反应便是邀请自己的亲朋好友: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集体狩猎的传统在购房过程中被自然延续——一起买的好处是,可以集体谈判。
平阳水头籍的炒房者陈立贤,极盛时曾手控家族亲朋1200多万的流动资金。“刚开始我们一个个去买,什么优惠都没有。”陈的妻子说。温州人买什么都要讨价还价的,买房为什么就可以例外?
团购带来的议价权效应被敏锐的温州媒体人观察到了,“炒房团”始现报章。
“炒房团是媒体和外地开发商、政府合谋的产物,当然,炒房团本身也乐观其成。”温州某报的一位房产部主任坦承,媒体出手,主要是看重背后的广告需求,“能使广告淡季不淡、旺季更旺。”在温州媒体,外地的地产广告迄今仍占到每年的20%以上。
最初发明温州看房团形式的、时任《温州晚报》主管经营副总编的陈康汉,多年后回忆自己的原始动机,也仅仅是为了换取上海开发商5个整版共30万元的广告。
2001年8月18日,第一个“温州看房团”,从温州坐火车抵达大上海。抵达当天,上海房地产协会便向陈转达了上海市一位领导“一定要把温州看房团服务好”的指示。
看房团效果显著,“看房的人,开发商,我们自己都会很满意。”同城的《温州都市报》《温州商报》等媒体纷纷效仿,“媒体看房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周五晚出发,周日晚返程,每周或更短时间组织一批,每批100-150人,有公务员、实业家、个体工商户、富裕的中产阶层等,报社负责交通、住宿,开发商请客吃饭,“购房团”浩浩荡荡开始游走全国。
“2002年、2003年左右最热闹,大伙集体砍价,九五折、九折都有,每次都有30%左右达成购房意向,有的还直接下订金。一个团近百套常有。”《温州晚报》的一名房产记者回忆。
除了三家媒体组织,受外地开发商委托的温州房产中介代理公司,也是主要的组织者,他们的销售佣金是楼价的1.5%。
媒体不遗余力的宣传和躬身延请的姿态,激发了温州人潜在的投资需求。
上述地产记者分析说,当时,温州的经济发展正经历一个调整期,人们突然对投资实业失去了信心。一向信奉“钱生钱”的温州各县小企业主,不得不寻找出路,温州人不喜欢买国债、炒股,“大家都觉得房子是实在的。”
而地区间楼市的差价也造就了炒房团的繁荣。在2001年左右,上海的陆家嘴,楼价每平方米也不过6000元,而当时温州各县的房价都已经接近此数。
更关键的是,和温州人买房一次付清不同,当时在上海买房,首付只需二三成,上海租金高,剩下的按揭完全可以靠租金偿还。
盛极而衰
而几次炒卖“烂尾楼”的大手笔,则将温州炒房团的影响推到极致。
2002年10月,温州商人王均瑶出手3.5亿元(内含2亿元装修费),收购位于徐家汇的“烂尾楼”金汇大厦,次年2月包装成上海均瑶国际广场,命名后楼价暴涨一倍,半年内投资回报率超过200%。
再其后,2003年11月,温州资本背景的飞洲集团收购上海“烂尾楼王”宝通大厦,回报同样惊人,轰动全国。
一时间,楼市言必称“温州炒房团”,“1000亿元炒房游资”,情节背景几乎一致的神秘买家,则成了媒体的集体游戏。彼时各地本受各种因素而起的楼价攀升,在迅速抛弃城市工薪层的同时,民愤被归咎于张扬而无所忌惮的温州炒房团之身。
2004年年中,在经历了金融政策及心理恐慌的连续打击后,飘红数年的中国房地产业开始遭遇泡沫化质疑,中国经济快车局部过热或全面过热激辩四起。
情势陡转而下。当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尹中立刊于本报的《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一文中,尹博士甚至要求对温州炒房团追究刑事责任,“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操纵市场罪。”
在舆论与民愤的压力下,上海、北京、杭州等地政府纷纷出手,限制期房转让、二手房市场征收高额个人所得税、购房实名制等强力举措纷纷出台,其意直指温州炒房团。
温州人第一次感到了寒冬和不受欢迎。对于前后迥异的态度,温州人觉得委屈——需要的时候,把他们当座上宾,风向一转,“我们成了大家泄愤的工具了。”
在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节节败退时,内陆二、三线城市的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却纷纷向温州炒房团抛出了绣球。
作为某种利好的符号,温州购房团早就进入到了政府、开发商和媒体营造地产繁荣的链条中。温州人的进入,成了解决商品房积压、房价和土地价格上涨的神奇灵丹——“楼房开盘,有没有温州炒房团来看,是好不好卖的象征”。
在炒房团路线大转折的2004年,沈阳房地产开发协会副会长王俊銮曾公开表示:我们非常欢迎温州人的到来,因为沈阳特别需要像温州购房团这样的团体进入沈阳,将辽宁和沈阳的房地产尽快盘活。
而在福建宁德,2003年温州人开始进入福建宁德,不到一年,宁德积压的商品房全部售罄。“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当地政府官员当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另一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事实是,同属2004年,成都一位房管局副局长曾坦承他们欢迎温州炒房团的逻辑,是觉得成都的房价和其地位不相符,“我们需要外力推一把,火一把。火一把不是要把泡沫吹出来,所以我们欢迎温州购房团。”
但受制于区域劣势以及楼价已然高企异常,异地炒房的商机再也不复当年动辄翻倍的黄金暴利。
2005年初,苍南人陈茹的母亲应邀去扬州考察房产市场时,已经失去了信心。“利润不大,大部分人都撤了,除了少数的职业炒家。”
二三线城市的风光很快不再,“买房一年两年,每平方市场价最多才涨个一千多,2005年开始,很多人就已经不再炒房了。即使购房,也是半投资半居住的性质。”经济学科班毕业的陈茹分析说,炒房的利润空间不再,人们自然会转战其他市场。
“这是温州炒房团发展的必然之路。”温州本土学者马津龙教授分析,和最初理性的自然选择一样:温州人较早尝到了房价大幅上扬的甜头,感觉到其他地区也会如温州一样房价飞涨,才会投向房地产。而现在,利润不再,而大部分出身中小企业主的房东主产业的资金链又如此紧张,炒房团自然失去了市场。
神化和神话的背后
争议依旧,它究竟是臆造的玩偶,还是中国楼市幕后提线的操纵者?
大量温州炒房团的资金,在初始阶段,都来源于众多“温州人”经商节余的流动资金。“炒房”本身,不过是温州民营资本在金融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
浙江是中国最市场化的几个省份之一,而温州人,则是在中国的市场化受益最深的群体之一。在市场化的环境下,资本的基本规律是向最能产生效益的地方流转,如此看来,温州人自己手中的钱投资什么、投资多少,似乎都是合理正当的行为。
诚然,在楼价飞涨的过程中,温州或者浙江炒房团,在全国市场中确实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数据显示,在全国,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50%的民间资本从事着房地产业生产和投资。但冷静分析,将之完全怪责于炒房团本身,显然并不明智。
地方政府的乐观其成,甚至积极推动,是硬币的另一面。
与资本逐利的魔鬼面相对,政府应代表大众利益,利用公共权力去制定规则,阻止或最大程度减小资本逐利性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与冲突。
但长期以来,部分地方政府,往往扮演着城市经营者的角色,楼价的上涨,自然会带来其土地出让收入的飞升,同时自然会拉高象征政绩的财政数字。
另一个事实上,温州炒房团的出现,在于中国起初房产需求的供不应求,在于未曾建立起合理公平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这一稀缺,造就了商品房不论高低,都能获全面而高速的发展。
诚如采访中浙江一名房地产公司老总所言,近年来,中央政府推动地方完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制度的前提下,市场自然冷淡。
而没有了市场,温州炒房团也必定如近期表现的一般,自然消亡。
·别了,温州炒房团 08/09/12
·易居研究:房地产泡沫研究及应对措施 08/09/10
·温州“炒房团”重返楼市? 08/08/07
·煤老板“力撑”SOHO中国 08/07/23
·传奇与梦想——深圳地产25年巡礼 08/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