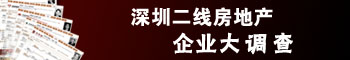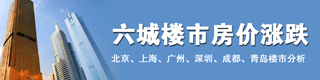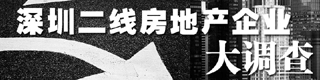房子的材料用过就扔不是我们的传统,况且这是一个十分划算的做法,房子造好,就已有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
那一天,在去宁波的火车上,或者,是从宁波返回杭州的火车上。我看见一座旧时民宅,单层,青瓦白墙,从檐廊看是一开间。我第一次意识到它的尺度如此之小。火车的高度提供了一个比平视略高的俯瞰视角,就显得它的瓦作曲面屋顶很大,但檐口的高度估摸只有两米略多。不远处是座小山,高度只在二三十米。我意识到是山决定了那座房子的尺度。那座房子就像一棵树种在山边。过去画的山水里,看似随便的房屋与塔,尺度当是真实的。那房子独处在稻田中,让人觉得孤独,远处几座新民居还算朴素,但尺度感大的多。决定尺度的已不是那山,而是远方城市中的建筑。又一次,我同时看到两个并存的世界,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那一天,我站在浙江台州路桥镇的河边,看河对岸的房子。房子破旧,连绵成带,但从中可以听到“一种傻呵呵的喃喃声过渡到刺耳的勤奋的嘈杂声”[注1],但仔细看,每一幢的界限实际上清晰可辩,是一种近似切分的音节。其中一段木作立面上,可看出一个木楼梯的剖面,与立面压扁在一个平面上,这种彻底的透明性让我着迷,我就在河边出神许久。
那一天,接学校通知去转塘看地。……那天看了转塘狮子山、象山等四块地方:典型的江南乡村土地,山都不大,50米高度上下。记得那天的事有点像一种相地仪式,人们谈的最多的是这山那山的气息如何……。地块最终落实在象山。我带画效果图的人又去看地,对他说不能随便用某张山的图片贴在图上,一定要下现场。我们就在现场拍了不少照片。我关心的首先在于一座总面积65000平方米,注定规模庞大的校园如何与一座不大的山共存,因为那山是先在的。山在建筑南侧,这群建筑将如何面对这座山,它们之间将说什么语言。二年之后,为了办“象山三望展”,我让研究生调出那组照片在电脑上按顺序拼接。研究生问我,这些照片焦距景深参差,甚至出入很大,视角会突然转折,是否需要在电脑上调整,或重新排序,我说不需要。结果让我有些讶异,拼出的照片和从建成后的建筑中看山的经验如此相似,一种思考着的目光,面对这个世界,沉静而温暖。视角的突然转折,好象有点走神。或者说,在房子未造之前,甚至未在脑子中出现之前,我已知道从建筑中,从建筑之间看山将会如何,但自觉的领悟它,却用了二年。……
那一天,我趴在图板上,面对场地原始总图,手衔铅笔考虑该如何下手。图上稻田沟渠纵横,如传统中国城市的平面,北京,长安,或者苏州。不同的是,没有任何超自然,没有任何象征主义的东西隐藏在其中。只有一种种植活动,一种秩序,一个框架,一种复制时间和节气的机器。于是设计改变为对某种先在的设计的修改。
那一天,路过我所住小区前的街道,眼前景象让我有点恍惚。街边的房子我拍过,一幢简朴的民国房子,里弄式的排屋,但已经没了院子。……一个师傅正在砌一个洗衣台,下面是清水砖,红砖、青砖夹杂着砌在一起,他就象一位哲学家,明白把两个关键句子分开的细微变化的重要性,一种小小的参差不齐和扭曲,就足以改变一切。……这些居民才是真正的城市居民,我的老师,他们明白建造房屋的目的:为了一种生活世界的再生。……
那一天,记得是2002年春节前,我去北大访张永和。北大西门到建筑中心的路上,应该是清朝的一处废园。房子已经不在,但山水还在,曲折反复。我突然意识到清朝工匠是怎么干的,他们先整山理水,然后选择房子的合适位置和高低向背。世上只有中国人这么做,用人工的方法建造一种相似性的自然,遵循某种不同的分类法和知识。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完全是观念性的。造房子,首先是造一个世界,这让我明确了转塘校园的场地做法,那些山边的溪流、鱼塘、茭白地和芦苇都应保留,顺应原有的地势,做顺势的改变。
那一天,我突然想再去绍兴看看青藤书屋。印象里那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房子,一处小院,围起一团宁静气息。布局有些随意,甚至让我无法清楚记得它的格局。肯定是什么偶然原因,让我无法成行。后来又几次想去,都未成行,再后来就搁下了去的欲望。于是,那处遮满绿荫的院子,就蜕变为一个梦想,隐含在最后建成的转塘校园之中。
那一天,我和妻子乘车去杭州梅家坞吃农家饭,途经一片种龙井茶的梯田。梯田石坎很长,道路和它很近的距离使它的两端超出视线之外,我对妻子说,这就是我想要的建筑基座,它具有某种超越视觉的力量,但却吸在土地上,轻轻的划定了地平线,划定了一个世界的界限。
……
那一天,艾未未和我一起在建筑系教学生用可乐瓶造房子。中午休息,无事可干,有点无聊。窗外正下着大雨,我建议去爬六合塔,体会一下那座塔在雨中如何。未未欣然同意,让我有点意外。前日乘车途经六合塔,我说我喜欢这座塔,未未说,不就是一座破塔吗,中国到处都是,有什么好看。雨大,无法在外停留,我们就直接进去。实际上,六合塔体积相当庞大,高达六十米,所在山体与象山近似,但走进塔内,体量感完全消失。每层塔六边,共十八扇完全相同的窗。我自每扇窗向外拍了一张照片,窗同,山同,但位置不同。我意识到把这十八张照片展开,就从内部决定了这组校园建筑面向青山回望的结构,从基座平台上,从院子中,门洞中,门框中,桥中,从房子之间狭窄的间距之中。塔离山很近,如从窗外逼来,我想总图上的三号楼可以逼的离山更近。中国的山与建筑的关系,从来不是景观关系,而是某种共存关系。当我们离塔,雨已停歇,山上腾起山岚。从外看塔,密檐瓦作压暗塔色,檐口很薄,材料与山体呼吸,塔如吸在半山,在如象山般多雾的气候中,塔甚至完全隐匿,变的很轻。那一刻,我明白了庞大坡顶建筑可能的立面做法,一种内外渗透性的立面,而那塔的轻和隐匿让我看见了象山校园的返乡之路。我心中所想的,对未未什么也没说,至于未未想了什么,我也没问。
那一天,海宁一位画家朋友带我去拜访乡下的一位老中医。老中医在当地颇有名望,已是八十几岁高龄,但步入他的院子,却是宁静朴素的很。南向单廊的平房,坡顶,座北朝南,房子东西向很长,走进室内,光线不亮,却很清朗,空气通畅。从室内望南面狭长的院子,亮的有些刺眼。这种室内外的光线反差,在江南的民居和园林中都有,我给这种室内的暗光起过一个名字,称为“幽”。窗上的窗格似乎故意压暗室内的亮度,这即是中国房子上窗户的意味。它不是像现代建筑的窗子是为了提供某种以卫生标准为依据的亮度,它是为了让人从室内向外看的,这才是真正的户牖,表达了面对世界的一种沉静态度,一种玄思气氛。走到户外,南檐廊阳光洒地,很是让人舒坦,我就想转塘校舍应该多做几次这种晒太阳的檐廊,窗子的光该如何控制,绘画教室需要均匀北光,就做南向单廊,通风会很好,用杉木在廊沿做可全开启的门扇,院子最高的有四层,门窗关闭,院子的内界就清晰,具有另人震撼的单纯性,门窗打开,实际上无人能始终控制它如何打开,院子就会具有轻快的多样性,阳光透过它又会如何,它会使院子变成那种双层底的魔术盒子,一种无内容的神秘感,想着就有点恍惚。老中医院子里种的不是一般花草,而是各种中草药,让我想起李渔的半亩园,或者中国的书院。我意识到书院真正的意义是一连串用院子围合起来的纯粹场景,其中不能缺了某些类植物和动物(或许如博尔赫斯在他杜撰的中国分类法中所描述的),作为读书之处,院子至少和室内一样重要,两者相合,才称是一个完整世界。我也想起童年时代住过的新疆大院,那是一个师范学院,院墙围起一个世界,正是停课闹革命的时候,老师们就变了农夫。校园里除了屋子都开垦成田地,种上包谷和蔬菜,一座田园般的学校,我曾在其中快乐欢叫着奔跑。在一个校园中,比建筑更重要的,是它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体会世界的场所结构,将选用几种建筑和植物类型,将勾带起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而我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在某种无目的的漫游状态中,一次又一次的从亲近身体的场所差异中回望那座青山,返回一种我们已经日见忘却的知识,使一种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被贬的生活方式得以活生生的复活。
……
那一天,我又去校园工地。工期只有一年,我下工地的次数也越来越频繁,每周至少三次。管工程的老师问我,瓦可不可以用旧的,旧的比新的便宜一半,我说当然可以,有多少用多少。中国房子的材料一向是循环利用的,用过就扔不是我们的传统,况且这是一个十分划算的做法,房子造好,就已有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旧瓦的气息、色泽也完全不同,它会使房子隐没在场景中,并与山相呼吸。杭州多雨,我开始想象这群房子在雨中的状态。现场运来的瓦愈见增多,除了瓦,又运来旧砖和石板。……堆在工地上,如一望无尽的海洋。后来我问管工程的老师,到底用了多少,他说统计了一下,超过330万片。
……
那一天,我登上7#楼48米处,下望,被施工中的体育馆瓦屋顶震撼。
……
那一天,我被工地上的一件事震惊。拆除脚手架后,发现教室的门均高2.7米,楼梯间的门却只有2.2米高度,高矮两种门直接并置。我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尽管我带着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花三个月把杭州市设计院的建筑施工图重画了一遍,但楼梯仍然是按原来的楼梯详图做的。管工地的老师们问我怎么办?把楼梯间的门拆了重做吗?我站在那里考虑很久,说,不用改,就这样吧。我喜欢追随偶然性,并试图去把握它。在中国的造园传统中,这种情况想必多次发生过,瓦解着我们关于建筑尺度的固定观念。有意思的是那种矮门,正好丈量了人的尺度,而它附近的门可能高达6米,这就是建筑中的蒙太奇。那扇高达6米的门在三号楼,就是我有意让它逼近山体的那座,门的比例是按范宽《溪山行旅图》做的。站在院内,透过那个门回望青山,就感觉很远。不知何时,大概是在临近竣工,象山已飞来满山遍野的白鹭,分白羽和褐羽两种,据说有数千只之多。
……
那一天,陪来访的美国罗德岛美院建筑系主任彼得去看既将完工的校园,看完,他问我一个问题:你认为,这座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
注1:引自[法]阿兰·罗伯—格里耶1963年文“雷蒙·鲁塞尔作品中的疑谜和透明”,见其批评文集《快照集》,湖南美术出版社“实验艺术丛书”。